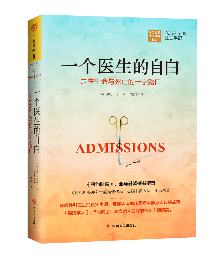
《一个医生的自白》
¥59 ¥59.80内容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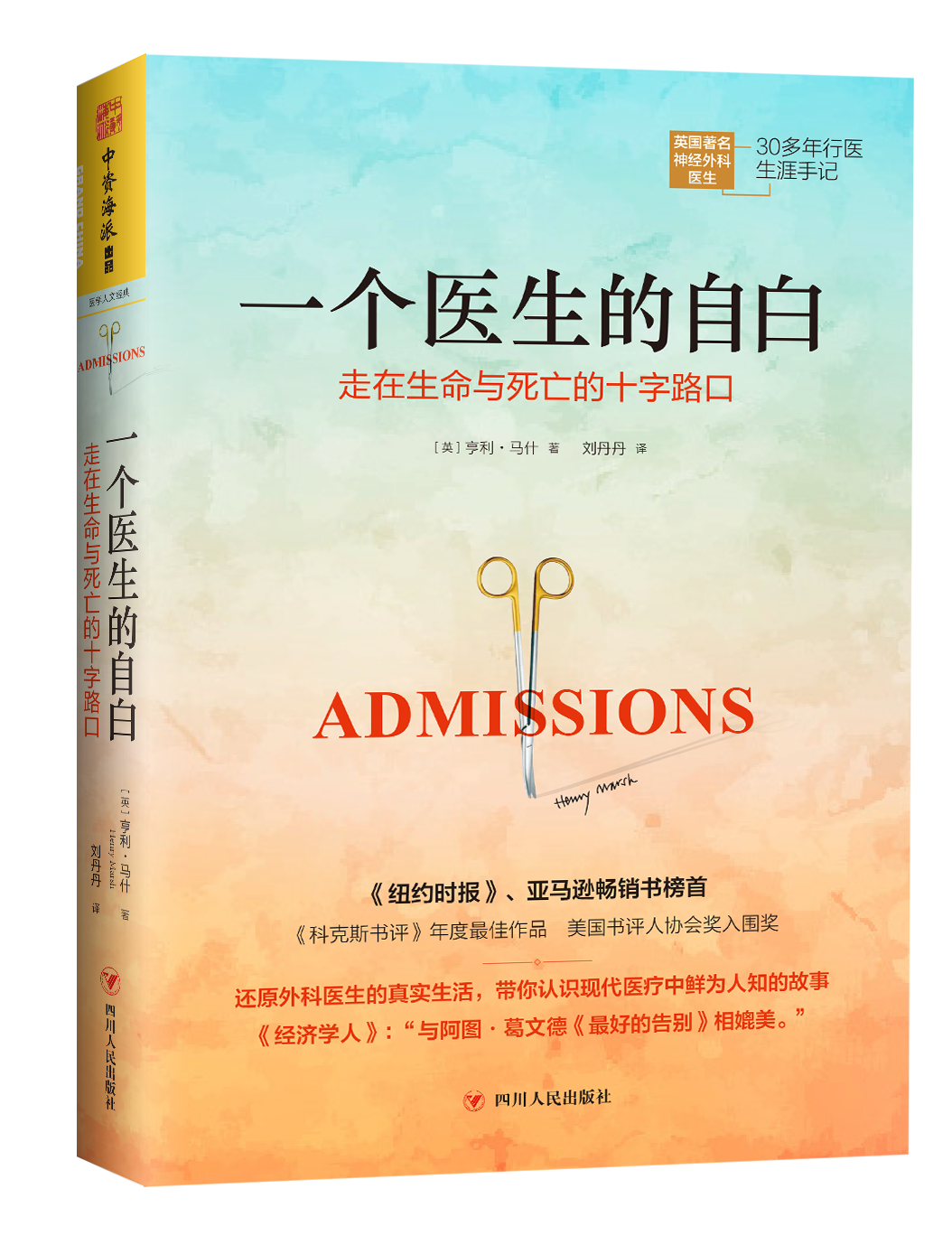

1. 荣登《纽约时报》、亚马逊畅销书榜首,《科克斯书评》年度最佳作品,美国书评人协会奖入围奖;
2. 本书是畅销书《医生的抉择》(已由我们出版中文版,已加印一次)作者亨利·马什的最新作品,《经济学人》评价其可与《最好的告别》(超级畅销书)相媲美;
3. 多家国内外知名媒体的报道和推荐,《医学界》(中国权威医学媒体)《自然》《科学》(国际权威科学杂志)、《泰晤士报》《经济学人》《卫报》《纽约时报》《纽约客》等
4. 这本书我们已经找到几位权威推荐人做推荐,他们分别是:
(1)林松教授
北京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四病房主任,美国神经外科学会资深会员,中国神经科学学会神经肿瘤分会委员;
(2)曹勇教授
北京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脑血管病和老年肿瘤专业病房副主任,主任医师;

亨利·马什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前沿现代医学。在从医的生涯中,他曾有手术成功后的振奋,也曾因失败身处毁灭性的低谷,但在内心深处,他从未动摇过对神经外科学的热爱。
在畅销书《医生的抉择》出版后不久,马什就从任职的伦敦圣乔治医院退休了,转而致力于国际人道主义医学援助,在乌克兰和尼泊尔继续做无偿的医学工作。这本书描述了他在这些国家的工作经历和遇到的困难,进一步表达了他对医学实践的见解。
这本书也谈到了马什为减少人类痛苦而肩负的责任。通过对医学生时期的回忆,他在书中塑造了一个外科医生的形象,并且探讨了医生这一职业中存在的种种困难,如医生处理可能性而非确定性时的艰难抉择,以及延长寿命的愿望可能给病人带来的悲剧性代价。
这本书是马什对自己30多年脑外科手术经历的回顾,在即将退休之时,他发现人生有种种不同的选择。对于什么是生活中重要的事情,他也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

亨利·马什(Henry Marsh)
英国著名神经外科医生,拥有30多年丰富的行医经验。英格兰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乌克兰神经外科手术先驱,英国笔会艾克理传记奖得主。
马什先在牛津大学获得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学位,后在伦敦皇家自由医院研修医学。1984年成为英格兰皇家外科医学院院士,1987年受邀担任圣乔治医学院阿特金森·莫雷医院的神经外科高级顾问。2010年,亨利·马什被授予大英帝国爵士勋章。2014年出版《医生的抉择》,一上市便成为畅销书,并被评价为“鲍斯韦尔式的传记”。
马什也是两部BBC纪录片的主角原型:《你的生命在他们手中》(Your Life in Their Hands)获得英国皇家电视学会金奖,《英国医生》(The English Surgeon)获得艾美奖最佳纪录片和上海白玉兰奖最佳纪录片。

《医学界》,中国权威医学媒体
顶尖脑外科医生坦诚吐露30 多年从医心得,不隐瞒、不避讳、不矫饰的真诚之作。
《自然》(Nature)
亨利·马什担任神经外科医生长达30 多年,并且名满天下。在这本充满思想性的书中(继《医生的抉择》之后的第二本书),他与我们闲聊了他的退休生活,以及在尼泊尔和乌克兰担任外科医生的经历。这本书充满了洞见,不仅讲述了人们对手术与大脑关系的担忧,而且谈论了衰老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养蜂、植树和做木工活的乐趣。
《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作者坦诚地为我们讲述着这些故事……虽然怀揣着不完美的英雄主义,叙述不免苛责挑剔,但尽管如此,这位医生还是招人喜爱。对于死亡和濒临死亡的思考,他的写作可以与阿图·葛文德(Atul Gawande)的《最好的告别》相媲美……与其说《一个医生的自白》讲述的是一位外科医生的故事,不如说它讲述的是一个“人”的故事,但无论从任何角度切入,这本书都非常精彩。

前言
第一章 在退休的三周前
守门人的小屋
一个个病例,一场场悲剧
逐渐褪去的盔甲
肿瘤才是罪魁祸首
第二章 伦敦
改变人生的决定
虽然痛苦,但我深爱
重症监护室里的小插曲
邓巴定律的关怀
第三章 尼泊尔
神秘而原始的国度
每个病人都有故事
医生心中有块墓地
富豪们牢牢霸占着转椅
有些话难以启齿
第四章 贫富只在一墙之隔
无名氏的光明未来
高楼外的流民
第五章 随时待命
术中唤醒
明智的选择
注定死于肿瘤的女孩
第六章 心脑问题
尼泊尔的首次门诊
晨练
来来往往的病人
黑暗中的灯塔
第七章 骑大象
大象的气息
天堂没有幼童之友
徒步旅行
一个漂亮的尼泊尔女人
只有医生才能理解
第八章 律师
卷入诉讼赔偿案
罪恶的繁华之都
第九章 多余的财物
手工制造
寿衣上没有口袋
第十章 重修小屋
打破的玻璃
燕子走了,再没回来
把小屋的过去留在过去
第十一章 记忆
从记事到现在
父母的故事
“健康营”
第十二章 乌克兰
伟大的分水岭
我的愤怒
第十三章 报歉
错误时有发生
没有任何存活的希望
第十四章 红松鼠
每个人都想离开
巨大的鸿沟
关于诚实与欺骗的演讲
小屋庭中半是苔
第十五章 太阳和死亡
除了等待,别无选择
希望自己是只海鞘
我做好了离开的准备
致谢

节选自第1章 在退休的三周前
肿瘤才是罪魁祸首
那一天晚些时候,我到楼上的重症监护室看望术后的病人们。那位年轻的罗马尼亚姑娘一切都好,尽管脸色看起来有些惨白,还有点发抖。一名护士正站在她的床头往手提电脑里输入数据,她抬头看了看,告诉我一切正常。在成排的重症监护病床中,威廉先生与这里隔了3个床,此刻,他已经醒了,笔直地坐着,眼睛直视前方。
我坐到他旁边,询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他转头看着我,沉默了一会儿。他那被癌细胞浸润和损伤的大脑,此时是一片空白,还是正在努力地组织思想?这些我都不得而知,甚至连他是否还是原来那个他都很难确定。我的很多病人在术后失去语言和思维能力,有时是永久的,有时是暂时的。等待是有期限的,之前,我只会待一小会儿。但是这次,我知道这样的情况可能不会再发生了,因此我静静地坐在那里,似乎过了很久很久。这或许也是我对过去的病人一种无声的致歉,因为我曾经不得不在回答病人的问题前就匆忙地离开。
“我会死吗?”他突然问道。
“不会,”我说,他似乎知道事情终究会怎样,这让我吓了一跳。“我发誓,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一定会告诉您。我总是对病人实话实说。”
他一定是明白了我的意思,所以他笑了,一种奇怪的、不合时宜的笑。“不,你现在不会死。”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远比死更糟糕。”
我又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但他似乎再没有其他什么要说的了。
早上7 点半,萨米如往常一样在护士站等我。他是传统模式下成长起来的一名初级医师,如果我已经在医院而他还没有到,这是他无法想象的事情。当我还是个初级医师的时候,在指导医师前离开医院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现在,在医生轮班工作的新体制下,
医疗训练的师徒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失了。
“她已经在接待室了。”他说。我们沿着走廊过去,坐在威廉夫人对面,我做了自我介绍。
“我很抱歉我们之前从未谋面。本来是蒂姆做这个手术的,但最后由我来做。恐怕我给您带来的并不是好消息,蒂姆是怎样跟您说的?”
通常,病人家属在听医生讲话时总是十分地专注,让你觉得好像一枚钉子正扎进你的身体。但是,威廉夫人只是悲伤地笑了笑。
“是个肿瘤,而且不能被完全移除。您知道吗?我的丈夫很聪明。”她接着说,“您没有见过他最佳的状态。”
“回想一下,您是什么时候发现事情不对劲的?”我温和地问道。
“两年前。”她立即回答道,“我们是7 年前结的婚,两个人都是再婚。他是一个亲切友好的人,但两年前,他变得不再是原来那个他,开始对我做一些奇怪的、令人痛苦的恶作剧。”
我没有问她是什么样的恶作剧。
“事情变得非常糟糕,”她接着说,“以至于我们都有些想要分道扬镳了,然后他出现了阵发性癫痫……”
“你们有孩子吗?”我问。
“他和前妻生有一个女儿,我们俩没有孩子。”
“恐怕我得告诉你,治疗也不能让他好起来。”我非常缓慢地说,“对于他的性格改变我们束手无策。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延长他的生命,不管怎样,他或许能够再活几年,但是慢慢地,他的情况会越来越糟。”
她用一种万念俱灰的表情看着我,茫然而无助,希望手术能够解除过去的种种恐惧,终结她的噩梦。“我以为是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她说,“他的家人将一切都归咎于我。”
“肿瘤才是罪魁祸首。”我说。
“现在我知道了,”她说,“我不知道该怎样……”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我告诉她我们还要等待移除部分的病理报告,如果病理报告显示移除的部分不是肿瘤,那么可能就要再次做手术。之后,唯一可能的进一步治疗就是化疗。但在我看来,这不可能让他好转。
我离开接待室,留下她和一名护士在那里。我认为在我离开房间之后,大部分病人家属都会痛哭。但或许,这仅仅是我的一厢情愿,他们可能更希望我待在那里。萨米和我沿着走廊回去。
“那么,”我说,“至少他们的婚姻走到尽头了,她可能会稍微好过一些,但是谁又能知道如何面对这样的事情呢?”
我想起15 年前第一次婚姻结束时的情形,想起前妻和我是如何冷酷愚蠢地对待彼此。我们两个人的大脑额叶上都没有肿瘤。那么究竟是大脑深处怎样的无意识活动,才让我们有了那样的行为举止?我惊恐地回想起来,在那段时间里,我对3 个孩子的关注是如何地少之又少。那时,我看过精神医师,他告诉我尽可能地去做一个旁观者。但我根本无法摆脱心中愈发强烈的情绪,因为我被迫离开自己亲手建造的家。熬过那段可怕的时光之后,我有了些许顿悟,但或许,这也仅仅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大脑里的情感消退了。
第二天,我去看望威廉先生。护士们告诉我,昨天我走之后,他曾试图在夜里逃走,她们不得不把门给锁上。这是一个美好的清晨,太阳刚刚升到伦敦南部的房屋顶上,阳光透过东面的窗户照进病房。他穿着睡衣站在窗户边上,我注意到睡衣上面装饰着泰迪熊。他的胳膊向两侧张开,似乎在拥抱清晨的太阳。
“您感觉怎么样?”我说,看着他轻微肿胀的前额,以及剃光的头上那一条缝合得很整齐的弧形刀口。
他没有回答,只是意味深长地朝我笑了笑,然后慢慢地放下双臂,一言不发、礼节性地握了握我的手。
两天后,病理报告证实,我送去的所有样本都被缓慢生长的癌细胞浸润了。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给威廉先生配备好长期护理人员,而在家里,他又无法得到有效的护理。因此我让助理医师把他送回当地的医院,也就是他癫痫首次发作时被送去的那家医院。那里的医生护士可能会找到解决的办法。肿瘤肯定会夺去他的生命,但无法确定是在几个月内,还是需要更长的时间。第二天清晨查房时,我发现威廉先生的病床上躺着另一个病人,而他已不知去向。
节选自第5章 随时待命
明智的选择
在伦敦的某些夜晚,我需要随时待命,因为半夜总会有电话打过来。但还不至于像德瓦那样,每天晚上都有人打电话过来。电话响起时,我就像被人从睡梦中拽出来一样,并且经常会有一种奇怪的幻觉,仿佛在电话铃声响起之前,我就已经决定要醒来了。这些急诊病人通常都是突发脑溢血(头部受伤或血管变薄弱而导致大脑出血),我必须决定病人是否需要做手术。有时候,不做手术病人就会死去,病人在术后会完全康复;有时候,病人不需要手术也能够活下来;有时候,无论你做什么,病人也终究会死;有时候,你也不确定是否应该做手术,也不确定手术后他们是否会康复。如果出血严重,无论手术多么成功,病人终会落下残疾,因为大脑是如此错综复杂又不堪一击,比身体的其它部位都更加难以修复。问题的关键在于残疾是否严重,病人术后是否会变成植物人?如果是那样的话,让他们死亡可能是更仁慈的做法。
仅仅依靠大脑扫描,我们不可能完全确定病人术后的康复情况会如何。如果我们像有些外科医生一样,不考虑可能的后果就对每一个病人做手术,那么我们就会对病人造成极大的伤害。对于病人家属而言,则是更大的痛苦。据估计,英国有7000人处于永久的植物人状态或仅有最低程度的意识。他们的存在不为人知,要么长期呆在看护机构,要么在家中由家人全天候二十四小时地照料。对于他们的痛苦,我们总是别过脸去,视而不见。完全不顾后果,对每一个病人都实施手术的做法相对简单,一个好的结果就能够证明所有坏结果导致的痛苦都是合理的吗?那么我又是谁,又如何有资格去甄别好的结果与坏的结果呢?医生不是上帝,没有决定生死的权利,但有时我们不得不如此,如果你笃信医生的职责是减轻人们的痛苦而不是不计后果地去拯救生命。
“病人26岁,昨晚淋浴时突然晕倒。看起来像是自发性颅内出血。可能是先天的脑动静脉畸形,部分钙化了。左侧基底神经节鼓起一个大洞,渗入中脑。从护理学上来讲,病人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是4。左侧瞳孔放大,在使用甘露醇和呼吸机之后,瞳孔恢复正常。CT显示有很多‘偏移’,可见基底池。现在已经给他插管并且使用呼吸机。”
“稍等。我看一下扫描。”我说着,从床边的架子上抽出笔记本电脑,将它平稳地放在膝盖上,几分钟之后,通过网络连接到了医院的X光系统。
“他不会恢复了,对吗?”
“是的。”我的住院医师说。
“你跟他的家人谈过话吗?”
“还没有。他还没有结婚,他的哥哥正在赶过来,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大概多久能到?”
“六点。”
“恩,或许我们可以等他哥哥来了再说。”
再解释一下,事情(也就是医生们常说的病史)是这样的。一个年轻人由于脑动静脉畸形而突然出现脑部出血。这是一种罕见的先天性疾病,脆弱的非正常血管纠缠在一起导致了脑部出血。出血发生在大脑左部以及部分中脑区域,而中脑对于保持清醒至关重要。从扫描上看,我认为即使进行手术,他也不太可能再恢复到有自理能力的状态。什么时候都不可能百分之百肯定,但对于他是否能恢复意识我都相当怀疑,更不用说重新行走或是讲话了。他的格拉斯哥昏迷评分是4,这意味着他处于深度昏迷状态。扫描显示他大脑中的压力不断增强(也就是住院医师所说的“CT上有很多偏移”)。他的左侧瞳孔已经放大,对光线没有反应,这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如果不做手术,他会在未来几小时内死亡。在使用了一种名叫甘露醇的药物后,他的瞳孔开始变小,这暂时性地降低了他的颅内压,所以做决定的时间十分有限。
我无法入睡,一个小时后就来到了医院。伦敦南部,太阳正在慢慢升起,一道长长的橙黄色光芒从医院的窗户照射进来。现在还特别早,走廊里阒无人声。但是重症监护室里已经非常忙碌了,到处一片嘈杂的声音。护士们正在准备换班,医护人员们在护士站周围来来往往。12张病床都满了,每个病床的周围都有用于静脉注射的输液架、注液泵以及监测器。监测器的屏幕闪烁着,不停地发出“哔哔”的声音,呼吸机在辅助病人的呼吸,不时发出轻柔的叹息声。护士们都在讲话,准备交接彼此的工作。
失去意识的病人们躺在床上一动不动,他们盖着白色的床单,静脉注射器插入胳膊上的静脉,嘴里连着呼吸机,身上连着鼻胃管和输尿管。有些病人头部还插着导流管和颅内压力监测线。
我的病人在远处的角落里,一位年轻人坐在床边,我朝他走过去。
“您是他哥哥吗?”
“是的。”
“我是亨利•马什,罗伯的顾问医师。我们可以过去谈一谈吗?”
我们握了握手,离开罗伯的床,走进会谈室。我要告诉他的是坏消息,我示意一位护士加入我们的谈话,这时住院医师也上气不接下气地赶了过来。
“我不知道你这么早就来了。”他说。
我示意病人的哥哥坐下来,然手自己坐到他的对面。
“你可能难以接受我的话。”我说。
“很糟糕吗?”他的哥哥问道。从我的语气和声音判断,他大概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
“他的脑部大量出血。”
“这位医生说,”他指向住院医师,“你会给他做手术。”
“是这样的,”我回答说,“恐怕事情要复杂得多。”
接着,我给他解释说,如果我们做手术让他活了下来,他也几乎不可能恢复到能够自理生活的状态。
“您比我了解他,”我说,“他愿意因为残疾而坐上轮椅吗?”
“他喜欢户外活动,喜欢航海……他有自己的船。”
“你们关系亲密吗?”
“是的,我们还是孩子时父母就去世了。我们是最好的伙伴。”
“他有女朋友吗?”
“现在没有,他刚刚和女朋友分手。”说话时,他将双手放在膝盖中间,眼睛盯着地板。
我们沉默了好几分钟。此时此刻,保持这种悲伤的沉默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是多年来的从医生活已经让我冷静了很多。
“没有任何希望了吗?”过了一会儿,他直视着我的眼睛问道。
“我怀疑没有。”我回答说,“但是老实讲,我们也不可能完全肯定。”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
“他讨厌变得残疾。有一次他告诉我,如果那样的话他宁愿去死。”
我什么也没有说。
“罗伯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认为这是明智的选择。”我缓缓地说道,尽管我们都没有明确说出彼此的决定。“如果他是我的家人,我也会这样做。我见过太多严重脑损伤的病人,他们生活得并不好。”
我们决定不再做手术。那天晚些时候,罗伯死了。在他脑死亡后,我们关闭了呼吸机,将他的其它器官用于移植。我想也许我错了,或许他会恢复到某种类似于能够自理生活的状态;或者他的哥哥错了,罗伯也许能够忍受残疾的生活;又或者罗伯会变的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自己,仅有最低程度的意识,无法理解自我的状态,认为生活也是幸福的。或许,或许……医生只处理可能性,不是确定性。有时候,如果你要做出选择,就得接受这样的事实,即你的选择可能是不正确的。一个好的决定可能会让你失去一个病人,但是却能让无数个病人和他们的家人脱离痛苦的渊薮。时至今日,这对我来说仍是一个难以接受的事实。当夜间接到类似病例的电话,如果我同意医院的值班医生做手术,那么我会翻个身继续睡觉;但如果我告诉他不要做手术,让病人死亡可能是更好的结局时,那么,在上班之前,我就会一直躺在床上,再也无法入睡。
